放大资金,增加盈利可能
配资是一种为投资者提供杠杆资金的金融服务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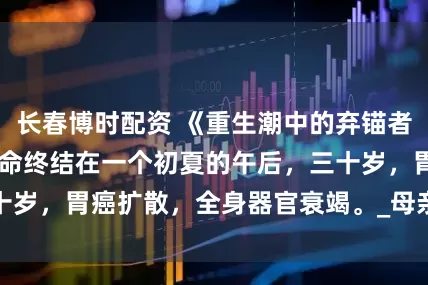
我的生命终结在一个初夏的午后,三十岁,胃癌扩散,全身器官衰竭。
意识消散前的最后一刻,我听见监护仪发出尖锐而绵长的悲鸣,像一道刺破灰色天际的闪电,宣告着我短暂而痛苦人生的终结。
穿着白大褂的医生,摘下口罩,脸上带着职业性的疲惫与同情。他握住我母亲的手,语气沉重地解释:“癌细胞已经全面侵犯了脏器,我们尽力了。主要是病人长期处于高度精神压力下,饮食作息紊乱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,她自己……把病情拖得太久了。”
我的母亲,张美芳女士,在听到这句盖棺定论的判词时,酝酿已久的情绪瞬间决堤。
她像一棵被狂风骤然折断的树,猛地扑到我的病床边,那哭声凄厉得足以撕裂空气。她捶打着自己早已不再年轻的胸口,用一种精心编排的、饱含戏剧张力的腔调嘶吼:“我的大宝啊!我的心肝!你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啊!你走了,让妈一个人可怎么活啊!”
她的悲痛是如此真实,如此具有感染力,以至于整个病房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。周围的病友和他们的家属,无不向这边投来怜悯的、感同身受的目光。他们看着这位几近崩溃的母亲,大概都在心里感叹着母爱的伟大与无私。
他们当然不知道。
展开剩余88%他们什么都不知道。
他们不知道,这位看似肝肠寸断的母亲,正是我胃里每一颗癌变细胞的培育者与浇灌者。我身体里的这场弥天大火,正是她用二十五年的时光,亲手点燃的。
自我有清晰的记忆开始,我的胃,就从未有过温暖的知觉。
餐桌上,永远有两道泾渭分明的风景。一道是属于我的:凝结着白色油花的剩菜,从冰箱里直接拿出来的、带着刺骨冷气的牛奶,甚至是边缘已经微微发酸的米饭。另一道,则是属于一个“幽灵”的:一碗用细瓷小勺轻轻搅动、散发着滚烫香气的鸡蛋糕,又或是一盘精心剔去鱼刺的清蒸鲈鱼。
我的母亲张美芳,会端着那碗热气腾腾的鸡蛋糕,坐在我的正对面。她会用小勺舀起一勺,小心翼翼地吹凉,然后递向她身边空无一人的座位,眼神温柔得能滴出水来。
她对着空气,泪光闪烁地低语:“小宝,我的乖女儿,快吃。你看姐姐多不懂事,又惹妈妈生气了。妈妈只能把最好吃的,都留给我们小宝了。”
小宝,我的双胞胎妹妹。
一个只活到了五岁的,永远停留在了那个夏天的名字。
那年夏天,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引发了郊区一处废弃工地的塌方。我和小宝,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,正在那片工地的空房子里玩捉迷藏。
轰然倒塌的预制板,将我们的世界瞬间拖入了无边的黑暗与死寂。
我和她被同一块沉重到令人绝望的石板压住了下半身,像两只被钉在标本板上的蝴蝶,动弹不得。浓重的尘土味和湿冷的泥土气息呛得我无法呼吸。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,我能清晰地听到她就在我身边,那微弱的、带着颤音的哭声,和我的哭声混杂在一起,像两只濒死的小猫发出的最后悲鸣。
不知过了多久,外面传来了嘈杂的人声和手电筒晃动的光柱。救援队来了。
我听到了我母亲的声音,那是一种被恐惧和绝望拉扯到极致,完全变了调的哭喊。
一个粗犷的男声在石板上方焦急地大喊:“下面是两个孩子对吗?听着!这块石板结构非常不稳定,我们移动它的时候很可能会造成二次坍塌!我们只能先救一个出来!家属必须立刻做决定!快!时间不等人!”
时间,在那一刻,仿佛被冻结了。
每一秒的流逝,都像一把生了锈的钝刀,在我的神经上来回切割、研磨,带来一阵阵尖锐的、几乎要将我撕裂的痛楚。
然后,我听到了那个声音。那个在此后漫长的二十五年里,化作我永恒梦魇的声音。
我的母亲,张美芳,用尽全身力气尖叫着,那声音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、近乎疯狂的决绝:
“救大宝!先救我的大宝!她学习好,脑子聪明!她将来肯定有大出息!先救她!”
石板在一阵刺耳的摩擦声中被缓缓撬动。
久违的光线像无数根烧红的钢针,狠狠刺入我的眼睛。
我被一双有力的大手从瓦砾堆里拽了出去。
被救出的那一瞬间,我下意识地回头。我看见,那块巨大的预制石板因为失去了我这边身体的支撑,瞬间失去了平衡,伴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,轰然砸落,将妹妹所在的那片小小的空间,彻底、永久地掩埋。
小宝的哭声,像被一把无形的剪刀,齐根剪断。
戛然而止。
从那天起,我,大宝,就不再是张美芳的女儿了。
我成了她“死去女儿”的替身,一个活生生的罪人,一个本不该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多余者。
“为什么死的不是你?”
这句话,像一道每日必须念诵的恶毒咒语,成了我们母女间唯一的交流方式。
我端起饭碗时,她会红着眼睛问我。
我躺下睡觉前,她会坐在我的床边问我。
甚至有一次,我考了全班第一,兴高采烈地把那张鲜红的奖状递到她面前时,她也只是一把将奖状挥落在地,然后死死地抓住我的肩膀,通红着眼睛,一字一顿地问我:“为什么死的不是你?”
她不再叫我大宝。她开始用“小宝”这个名字来称呼我。
她逼着我穿上小宝生前最喜欢的那条粉色连衣裙。那裙子对于当时的我来说,已经太小了,紧紧地箍在我的身上,勒得我喘不过气,像一层屈辱的、无法摆脱的皮肤。
她会拿出小宝唯一的一张遗像,抱在怀里,一遍又一遍地给我讲述,小宝是多么的乖巧可爱,多么的善良懂事,多么的讨人喜欢。
“你要替妹妹活着。”她用指腹轻轻抚摸着相片上小宝稚嫩的脸庞,眼神却越过相片,像两根淬了剧毒的钢针,狠狠地扎在我的身上,“你要活成她的样子,连同她没活成的那一份,一起给我好好地活下去!”
于是,我的人生被强行按下了格式化键。
我剪掉了自己心爱的长发,因为小宝一直是清爽的短发。
我放弃了自己最喜欢的蓝色,因为小宝的世界里只有粉色。
我不敢再放声大笑,因为我妈说,小宝笑起来总是抿着嘴,很文静。
我成了一个被抽去灵魂的提线木偶,按照她编写的剧本,日复一日地扮演着一个早已死去的妹妹。
可我演得再像,终究是赝品。
她总能从我身上找到各种各样的破绽,然后以此为借口,对我施加无休止的折磨。
饭菜凉了,是我的错,因为我没有小宝那么体贴。
家里地板没拖干净,是我的错,因为我没有小宝那么勤快。
她在单位受了领导的气,回到家,一言不发,迎面甩来的就是一个响亮的耳光,打得我眼冒金星,耳中轰鸣作响。
“你这个丧门星!克星!如果不是为了救你,小宝根本就不会死!你为什么不去死!”
胃部的疼痛,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。
起初只是隐隐的、不易察觉的绞痛,后来逐渐演变成剧烈的、如火焰烧灼般的疼痛。我捂着肚子告诉她我胃疼,她只是用眼角的余光冷漠地瞥我一眼,嘴角挂着一丝残忍的讥诮:“装什么可怜?你妹妹被埋在冰冷的地下,比你疼一万倍。”
我学会了忍耐。
忍着胃部的灼痛,忍着长期的饥饿,忍着她眼神里无处不在的怨恨和随时可能爆发的暴力。
我用近乎自虐的方式学习,考上了省里最好的重点大学。我以为,这张录取通知书,会是通往自由的船票。
我把通知书递给她看,她只是漠然地扫了一眼,然后随手就扔进了旁边装着果皮的垃圾桶。
“有什么用?你妹妹去不了了,你去读大学又有什么用?”
大学四年,我靠着国家助学贷款和在餐馆里疯狂洗盘子活了下来。我天真地以为,等我毕业了,工作了,经济彻底独立了,我就能像壁虎断尾一样,彻底摆脱她的阴影。
但我错了。大错特错。
她像一道无法摆脱的诅咒,死死地笼罩着我的人生。
她会像个疯子一样冲到我工作的公司,当着我所有同事和领导的面,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,控诉我这个害死妹妹的不孝女,现在飞黄腾达了,就要抛弃含辛茹苦把她养大的老母亲。
同事们那些同情、怜悯又带着一丝探究的目光,像无数根细密的钢针,将我扎得体无完肤,无处遁形。
我开始频繁地换工作,像个惊弓之鸟一样不停地搬家。
可无论我躲到哪个角落,她总有办法找到我。她就像一只嗅觉灵敏的猎犬,而我,是她命中注定无法逃脱的猎物。
三十岁生日那天,我独自一人坐在出租屋里,手里攥着那张胃癌晚期的诊断书。
看着那几个冰冷的黑色宋体字,我竟然笑了。
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。
原来,报应真的存在。
只是这报应,没有落在那个施暴者的身上,而是精准地降临在了我这个苟延残喘的受害者身上。
也好。
这样也好。
我终于可以,不用再“替妹妹活着”了。
我终于可以,去做回我自己了,哪怕代价是死亡。
我走上了医院住院部顶楼的天台。
纵身一跃的瞬间,风在耳边激烈地呼啸,像一首悲壮的送葬曲。二十五年来的痛苦、压抑、屈辱与绝望,像一部被按了快进键的黑白电影,在我眼前飞速闪过。
我以为,我的灵魂会坠入万劫不复的无边地狱。
但没有。
当我再次睁开眼睛,我又回到了那片熟悉的、令人窒息的黑暗中。
身上是石板沉重如山的压力,耳边是小宝微弱得像随时会熄灭的哭泣。
我……重生了?
我竟然重生回了五岁那年,那个决定了我一生命运走向的塌方时刻。
文章后序
(贡)
(仲)
(呺)
欢-阅-推-文
发布于:浙江省倍悦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